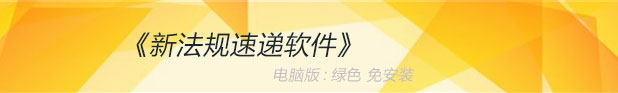[ 溫躍 ]——(2025-11-4) / 已閱8632次
5.1.4 不少學者認同費爾巴哈的寬厚和仁慈,主張對牽連犯不數罪并罰。“之所以對牽連犯按一罪處理,是因為考慮到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或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在經驗法則上常常存在一種伴生關系。”(大谷實:《刑法總論》)
“犯罪行為人之目的僅欲犯一罪,只因其實施之方法或因其實施之結果觸犯其他不同罪名,就行為人心理上之惡性程度而言,與本欲犯數罪之情形究不同,如作數罪并罰,未免過苛。”(黃村力:《刑法總則比較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97年版)
“因為相互牽連的數行為存在緊密的聯系,通常相伴實施,這反映行為人具有較小的主觀惡性和可非難性。目的行為與原因行為是行為人反規范意識的主要指向,手段行為與結果行為相對于主行為來說是一種預備行為、方法行為或維持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雖然具有數個反規范意識,但與并罰數罪下分別形成的反規范意識相比,其在可譴責性上確實具有值得寬宥之處,因而與并罰數罪相比在量刑上理應有所區別。”(王明輝《非并罰數罪研究》)
5.1.5問題是一個人數個行為觸犯數個罪名原則上是要受到數罪并罰的,如果數個行為觸犯數個罪名只按照一個罪名處罰,不僅放縱了犯罪甚至是鼓勵犯罪。比如,一個罪犯強奸了婦女后把受害婦女殺害了,只追究其殺人罪而忽略不計其強奸罪,或只追究其強奸罪而忽略不計其殺人罪,很難取得社會共識,而會引發社會公憤的。如果采取費爾巴哈目的和手段二選一的思路,認定其殺人是為了掩蓋強奸的行為,是強奸罪的一個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強奸是目的,殺人是掩蓋強奸罪行的手段,甚至在強奸前就考慮好了:強奸完成后就把女人殺了。以目的和手段來理解強奸行為和殺人行為的關系,有何不可?憑什么認為手段行為一定在目的行為之前或之中?而不能在目的行為之后?在強奸過程中殺害婦女才是目的和手段的牽連犯?才能獲得二選一的優惠政策?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的區分完全是因人而異的,對于有些人來說是手段行為,對另一些人來說可能是目的行為。對一些人來說偽造公文是詐騙的手段,對另一些人來說,詐騙行為是為了驗證偽造公文技藝的手段。在一些人看來兩個無關聯的犯罪行為,在另一些人看來就是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系。手段和目的,完全是人為的設置,一人犯數罪,只要其把其中一些犯罪行為解釋成另一些犯罪的手段或方法,就可以借助牽連犯的擇一重罪處罰原則而使得手段、方法行為觸犯的罪名都忽略不計了?誰說手段、方法都必須是有效的?必然途徑或結果?為了強奸一個女子,使得其不敢反抗,犯罪人可能把旁邊一個無辜的人殺了,殺人成了強奸的恐嚇手段,殺人罪與強奸罪是牽連犯嗎?要求牽連的手段與目的行為之間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強奸不一定都要殺人,因此殺人行為與強奸行為不是牽連關系?盜竊槍支與殺人之間也不是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此,盜竊槍支后用盜竊的槍支殺人也不是牽連犯而該數罪并罰?那么偽造公文與詐騙之間也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詐騙也不是必須偽造公文的,憑什么認為偽造公文后詐騙是牽連犯而擇一重罪處罰?
5.1.6 德國的普珀教授認為“除了馬戲團演員外很少有人同時做內容不相關的事情。實施犯罪時往往通過一個甚至幾個身體上的動靜實現,這將是用一個或者其它兩個為了同一目的手段實現目標的形式。”如果以犯罪人的真實想法來認定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那么盜竊槍支后用盜竊的槍支殺人就是目的和手段關系,就是牽連犯。換句話說,數 行為觸犯數罪名的犯罪,很難排除行為人主觀上沒有牽連的意圖,即使行為時沒有牽連,在訴訟時也會宣稱具有牽連意圖,而很難證偽這樣的意圖。如果不以行為人對行為的目的和手段的主觀想法作為認定目的和手段的標準,那么所謂的客觀說主張的必然性、因果性都會導致荒謬不堪的結果。最典型的牽連犯的范例偽造公文進行詐騙活動,就不存在必然性和因果關系。由此可見,主張目的和手段認定客觀說的學者最后不得不搞出個“通常性質說”來進行理論特設:即大多數情形下,犯罪分子會偽造公文進行詐騙活動,所以,偽造公文與詐騙行為是手段和目的關系,因此成立牽連犯,擇一重罪處罰。但大多數情形下,犯罪分子不會偷槍來殺人,因此,偷槍的犯罪行為與殺人行為不是手段和目的關系,不成立牽連犯,需要數罪并罰。
5.1.7 有學者努力為牽連關系尋找數行為間的“緊密關系”:“行為人為方便搶劫銀行而事先盜竊他人的車輛。從行為人的角度看,盜竊汽車確實是搶劫銀行的一種手段,但基于規范限制因素的考量,該種情形下的盜竊與搶劫只是偶然地發生關聯,不屬于一種緊密的伴生關系。行為人為了詐騙保險金而實施放火、殺人等行為,其數個行為間的聯系也較為松散,并沒有形成一種能夠使行為人責任程度有所降低的手段目的關系。行為人以取財為目的而盜竊他人的皮包,后發現皮包中有一支軍用手槍,便將該手槍非法占有。在該案中,行為人只具有盜竊普通財物的故意,并無盜竊槍支的故意,也沒有將非法占有槍支作為盜取財物的一種手段。因此,其盜竊財物的行為與非法持有槍支的行為之間也是一種偶然的先后關系,并未表現出緊密的“牽連關系”。” 我認為牽連關系研究中主張前后行為是“緊密的伴生關系”是荒謬的,伴隨犯作為共罰行為的一種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求牽連犯具有伴隨犯的特征是錯誤的。“沒有形成一種能夠使行為人責任程度有所降低的手段目的關系”的說法是荒謬的,因為首先要判斷出具有牽連關系,然后才能降低行為人的責任承擔,不是先判斷出行為人的責任程度再判斷是否具有牽連關系,這是倒因為果。牽連犯從客觀上是給不出判定標準的,從主觀上給標準會出現隨意性。其實,給予牽連犯優惠待遇是費爾巴哈的主張,就是給予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共同觸犯兩個罪名時,給予一定的寬恕,但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的區分本身就是主觀標準,不存在客觀標準,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的區分也不是純客觀標準,因果關系本質上是社會共識的認定,物理世界的因果關系到法律上也可能不與認定是因果關系。因此,牽連犯脫離不了主觀標準來認定,所謂主客觀相結合的認定,只是折中主義的淺薄。既要符合主觀標準又要符合客觀標準?對于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來說,這是荒謬的。其實,牽連犯多數案例都是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時是否給予寬恕的問題。在此只有主觀標準,不存在客觀標準。
5.1.8 其實,費爾巴哈關于牽連犯的觀點只是一個傾向性的表態:他認為行為人為了實施犯罪而手段或結果上觸犯其他罪名時,是該給予寬恕的,不要給予數罪并罰而只要擇一重罪處罰即可。英美法系不理睬費爾巴哈的說法,行為人實施數行為觸犯數罪名時,不論是否存在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結果行為等關系,一律數罪并罰。你可以理解英美法系不夠寬恕,不夠仁厚,也可以認為費爾巴哈亂施恩惠放縱犯罪,但這里不存在牽連情形下行為人主觀惡性較小或社會危害性較輕問題。從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較輕角度為牽連犯辯護,肯定擇一重罪處罰;從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均觸犯刑律,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并不比無牽連的數罪輕微,不值得寬恕,應該數罪并罰,這兩種辯護思路只是兩種對立的傾向和信仰,對立雙方的學者均給不出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大小的依據,無非就是表明牽連犯值得寬恕或不同意寬恕。鑒于英美法系均不寬恕牽連犯,我國相當一部分學者主張廢除牽連犯,即統一按照數行為觸犯數罪的數罪并罰處罰,高銘喧教授認為:第一,無論是從形式上還是從實質上來看,牽連犯均屬于數罪;第二,根據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對牽連犯應當實行數罪并罰;第三,對牽連犯實行數罪并罰是刑法學發展的必然要求;第四,對牽連犯進行數罪并罰符合我國刑法的目的。(高銘喧,刑法專論(第二版))“罪數問題在理論上復雜化的原因之一是牽連犯的概念引發出來的”( 儲槐植:《論罪數不典型》) 我認為是否給予牽連犯寬恕免除其適用數罪并罰的規則,這是一個價值選擇問題,不存在正確與否的問題。現在中國大陸很多學者主張不予寬恕這種情形,因而主張放棄牽連犯的分類,對于所有手段和目的或行為和結果觸犯不同罪名的,一律適用數罪并罰規則,不再給予特別優惠政策。我認為這不過是社會共識轉變問題。英美法系一直沒有給予牽連犯寬恕政策,也沒有讓人感覺到苛政猛于虎。
5.1.9 牽連犯是否廢除的問題實際上不存在理論上的困惑,無非就是對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構成的數罪是否給予寬恕的問題,廢除派就是不給予寬恕,一律按照數行為觸犯數罪的并罰處罰,保留派實際上就是想給予數罪中如果存在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或行為的結果又觸犯另一罪名時給予寬恕,不要數罪并罰。由于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在認定上難以避免主觀隨意性,不確定性,且免除手段行為或方法行為的可罰性,從主觀惡性或社會危害性上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據,把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數罪并罰并不存在所謂禁止重復懲罰原則的問題,也不存在不得不使用某種手段犯罪的期待可能性問題,因此,我基本上贊同對于牽連犯涉及的數行為觸犯數罪問題不論其是否涉及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均按照數罪并罰處理。
5.1.10 各國司法實踐中都存在把數行為認定為牽連關系而無法取得社會共識的情形。雖然通常認為偽造公文與詐騙罪之間存在牽連關系,但并不能說明為何盜竊槍支殺人卻要數罪并罰。我認為同樣是手段和目的之間的牽連關系,偽造公文與詐騙罪認定是牽連犯,而盜竊槍支殺人不承認是牽連犯,要數罪并罰,這里表明是否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完全是個社會共識問題,給不出理性的界限。
【案例】即使行為人當初沒有作為手段、結果而實施其他犯罪的意圖,判例也認為是牽連犯。例如,以夜里行奸的目的侵入他人的住居后,竊取了他人財物時,認為是侵入住居罪和竊盜罪的牽連犯(大判大6·2·26錄23·134);行為人企圖裝成強盜威脅家人而侵入了他人的住居后,在屋內產生殺意而殺害了人時,認為是侵入住居罪和殺人罪的牽連犯。
(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P426)我認為這里殺意的后起的,說侵入住居于殺人之間存在手段和目的的牽連,非常勉強。可見不同的法治環境,社會共識有差異。
5.1.11 目前廢除牽連犯最大的障礙是我國現存立法和司法解釋中對于涉及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的牽連關系數罪的情形,有一些是直接規定擇一重罪處罰或擇一重罪從重處罰,排除了適用數罪并罰。
【立法例】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對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并罰。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
如果理論上廢除牽連犯,一律采取數罪并罰,那么如何對待現行立法和司法解釋?很多牽連犯的立法和司法解釋已經實施多年,司法機關已經習慣了擇一重罪處罰或擇一重罪從重處罰,改變一個已經實施多年且根深蒂固的司法共識,非常困難。我的看法是在廢除了牽連犯概念后,這些立法、司法解釋可以歸入共罰行為來處理,納入社會共識的范圍。有學者一方面論證牽連犯的特征和判定方式,另一方面又說牽連犯的處罰應該數罪并罰。牽連犯理論的價值就在于排除數罪并罰,如果牽連犯仍然適用數罪并罰,那么區分牽連犯就毫無意義和價值了。高老等主張廢除牽連犯,實際上是主張數行為觸犯異種數罪一律數罪并罰而不區分出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或結果行為的牽連犯作為數罪并罰的例外,換句話說沒有必要再去尋找牽連特征和區分牽連犯這個分類了。
5.1.12我認為我國刑事立法中的選擇性罪名立法,實質上就是法定的牽連犯,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按照選擇性罪名觸犯幾個罪名就列舉幾個罪名,按照一罪以該選擇性法條的法定刑處罰。如果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涉及同一宗假幣的犯罪行為,司法解釋依然規定作為牽連犯擇一重罪處斷,而不適用數罪并罰規則。對于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并罰。我對于這種根據犯罪對象區分牽連犯和實質數罪的司法解釋,有不同意見:在廣場上隨機槍殺三人,犯罪對象不同,構成三個故意殺人罪或三個危害公共安全罪?(同一行為不同犯罪對象)如果行為人強奸一個女人,然后殺掉另一個女人,數罪并罰;如果行為人強奸了一個女人,然后殺掉了這個女人,擇一重罪處罰?(不同行為,同一對象擇一重罪處罰,不同對象就數罪并罰)
【案例】以詐欺保險金為目的進行的放火與保險金的詐欺(大判昭5·12.12集9·893);由于誤射造成的業務上過失傷害與其后以殺意進行的殺害(最決昭53·3·22集32·2·381);殺人與損壞尸體(大判昭9·2·2集13·41);殺人與尸體遺棄(大判明43·11·1錄16·1812);尸體的遺棄與損壞(最判昭27·6·24集6·6·804);墮胎與殺害出生兒(大判大11·11·28集1·705);監禁婦女與強奸致傷(最判昭24·7·12集3·8·1237等);監禁和傷害(最決昭43·9·17集22·9·853);竊盜與其后的強盜(最決昭32·3·5集11·3·985);竊盜與利用盜品進行的詐欺(最判昭25·2·24集4·2·255等);竊盜的教唆與被教唆者所竊取物品的有償讓受(大判明42·3·16錄15·258);強盜殺人與為了隱滅犯罪痕跡而進行的放火(大判明42·10·8錄15·1293);強盜犯人的殺人與尸體的遺棄(大判昭13·6·17集17·475);橫領與作為隱蔽其手段的竊盜(大判大2·3·4錄19·291);業務上橫領與為了隱蔽其犯罪痕跡而實施的使用偽造的公私文書(大判大11-9·19集1·453);強奸與為了隱蔽犯罪痕跡的殺害婦女(大判昭7·2·22集11·107);賭博場的開張與賭博(大判大4·3·30錄21·319)等。(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P429)上述日本判例均認為都不是牽連犯,而是作為數罪并罰來處理。我認為日本對于強奸與為了隱蔽犯罪痕跡的殺害婦女不按照牽連犯處置而是數罪并罰,足以否定其牽連犯理論所主張的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的牽連關系。以詐欺保險金為目的進行的放火與保險金的詐欺也是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的牽連關系,日本判例數罪并罰而不按照牽連犯處置,說明牽連關系理論不能作為判定牽連犯的普遍規則使用,牽連犯理論(不論主觀說、客觀說還是折中說)都不足以用來作為排除數罪并罰的普遍適用規則。
5.2 吸收犯
【案例】甲盜竊了一個包裹,卻發現里面裝有槍支、彈藥,于是將槍支、彈藥私藏起來。在本案中,首先,甲的行為構成了普通盜竊罪,而不是盜竊槍支、彈藥罪;其次,甲的行為還構成了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有學者認為這兩罪之間構成吸收關系。
【案例】行為人先對同一被害人用投毒的方法殺害,沒有成功,幾天后又用刀將同一被害人殺死。有學者認為行為人實施的數個行為是同質的,一個是殺人未遂,另一是殺人既遂,由于它們共同侵害同一對象之同一個法益,所以只能評價為一罪,既遂行為吸收未遂行為。
5.2.1 臺灣刑法學說中,傳統意義上的吸收犯僅指一罪之構成要件當然包括他罪,或所犯之罪是為犯他罪必然得由之方法或必然可得之結果。(蔡墩銘主編: 《刑法總則論文選輯》(下) )有學者認為:“吸收犯是指事實上數個不同的行為,其一行為吸收他行為,僅成立吸收行為一個罪名的犯罪。 數行為必須觸犯不同罪名”。有學者認為“吸收犯是指在一個犯罪過程中,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犯罪行為因屬于同一罪質, 而由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的犯罪形態,僅以吸收之罪論處的犯罪形態。”
5.2.2趙秉志教授認為:“所謂吸收犯是指行為人實施數個犯罪行為,因其所符合的犯罪構成之間具有特定的依附與被依附關系,從而導致其中一個不具有獨立性的犯罪被另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犯罪所吸收,對行為人僅以吸收之罪論處,而對被吸收之罪置之不論的犯罪形態。”(趙秉志主編《刑法新教程》)“吸收犯的數個犯罪行為之間必須具備“基本性質的一致性”,而且“數個犯罪行為必須侵犯同一或相同的直接客體,并且指向同一的具體犯罪對象”“在行為人實施的數個犯罪行為中(以下均以行為人實施兩個犯罪為標準論述),一個犯罪行為不具有獨立性,而另一個犯罪行為具有獨立性,前者以不同的表現形式依附于后者而存在,這是數個犯罪行為之間形成吸收關系的最基本的原因。基于一個犯罪行為與另一個犯罪行為的依附關系而成立的數個犯罪行為之間的吸收關系,最終取決于類型不同,但基本性質一致的犯罪構成所固有的特定聯系,并應以此為基準而予以認定。”。(趙秉志主編《刑法新教程》)”趙秉志教授用數個行為間具有的“依附關系”來為吸收關系做解釋,但他無法進一步解釋清楚為何數行為間存在“依附關系”?數行為間簽訂了“賣身契”?“勞動合同”?還是因“真愛”而具有人身依附關系?他看似解釋了什么,其實什么都沒有解釋。
5.2.3 暫且不去討論罪之吸收還是行為之吸收。如果說費爾巴哈區分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從而主張寬恕地給予二行為觸犯的罪名按照一重罪處罰而完全忽略不計手段行為或目的行為觸犯的罪名,體現了費爾巴哈寬廣仁厚的胸懷,不以數罪并罰把犯罪人一棍子打死的善意,那么在吸收犯問題上主張一犯罪行為吸收另一犯罪行為就顯得莫名其妙和強詞奪理了。
5.2.4 行為人犯罪行為之間完全不存在客觀的“吸收”屬性,所謂的A行為“吸收”了B行為,實際上是以A行為觸犯的罪名定罪量刑,而對B行為忽略不計,僅此而已。在此,“吸收”僅僅是個生理學的比喻說法。根本的問題在于學者主張的“吸收”與“被吸收”完全不是犯罪行為本身的屬性,完全是人為地規定A行為“吸收”了B行為。如果你問憑什么說A行為能夠吸收B行為?相信大多數持有吸收說的學者說不出所以然來,有的學者用“重行為”吸收“輕行為”“前行為吸收后行為”“后行為吸收前行為”來搪塞,給人以一種虛假的理論幻象,好像行為之間能夠“吸收”,如同你吃了一個西紅柿,這個西紅柿被你吸收了一樣。接著的問題是:憑什么說重行為能夠吸收輕行為?一個人兩個行為分別觸犯刑法時,觸犯重罪的行為都能夠吸收觸犯輕罪的行為嗎?在什么條件下重行為能夠吸收輕行為?在什么條件下重行為不能吸收輕行為?所有的前行為都吸收后行為嗎?什么情況下后行為吸收前行為?僅僅說“前行為吸收后行為”或“后行為吸收前行為”不能作為吸收犯理論的根據。因為不是所有前行為都吸收后行為的,也不是所有后行為都吸收前行為的。
比如,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其作品又銷售的,侵犯著作權行為是銷售侵權復制品行為的前階段,應屬共罰的前行為,但其最高法定刑是10年有期徒刑,而后者為5年有期徒刑;若以“后行為”銷售侵權復制品行為來包括地處罰, 即適用“后行為吸收前行為”規則,是不公正的。
比如,侵占他人財物后又毀壞的,毀壞行為屬于共罰的后行為,但侵占罪的最高法定刑是5年有期徒刑,而故意毀壞財物罪是7年有期徒刑;若以“前行為”侵占罪來包括地處罰, 即適用“前行為吸收后行為”規則,也是不公正的。
因此,當人們問為何A行為吸收B行為?你回答道:因為前行為吸收后行為。等于什么都沒說。或相當于說:因為A行為喜歡B行為,或因為A行為噶屁了B行為,或A行為消化了B行為。
【案例】從社會危害性來看,偽造車、船票的行為嚴重擾亂了國家對有價票證的正常管理秩序,其性質明顯重于詐騙出售的行為,因此以偽造行為吸收詐騙出售的行為,僅論以偽造車、船票罪定罪處罰。
【案例】一個人非法制造槍支,而后將其所制造的槍支予以私藏,行為人實施的私藏槍支的行為被之前的制造的槍支行為所吸收。
如果重罪具有吸收輕罪的能力,那么殺人后發現死者錢包,拿走錢包的盜竊罪要被殺人罪吸收嗎?顯然不。重罪吸收輕罪的規則只是解釋規則,不是預測規則,也不是判定規則,不能在所有出現重罪行為和輕罪行為時作為規則來判定數罪并罰還是僅僅以重罪吸收輕罪定罪處罰。只有在立法或司法解釋中規定A行為吸收B行為,以A行為定罪處罰而完全忽略不計B行為時,學者們會給出解釋:之所以A行為吸收B行為,是因為A行為是重行為,B行為是輕行為,這是重行為吸收輕行為,或這是前行為吸收后行為。由此可見,所謂“吸收”概念根本就不是行為的客觀屬性,也不是罪的客觀屬性,吸收是個比喻說法,“A吸收B”其意思是B融入了A,B喪失了獨立存在。你吃了西紅柿,西紅柿被你吸收了,西紅柿喪失了獨立存在。對于行為來說,不存在A行為吸收B行為的問題。完全無法根據“行為吸收”理論來判定任意的兩個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吸收”關系,更無法根據吸收理論來判定兩個罪之間是否存在吸收關系。
5.2.5 在同一罪名之間的吸收理論就更加荒謬了。通行的說法是“既遂行為“吸收”預備行為”,“既遂行為吸收未遂行為”。好像既遂行為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似的。其實,既遂行為符合立法上的構成要件其可罰性顯而易見,預備行為和未遂行為、中止行為本身不符合構成要件,因而虛構或說“理論特設”了“修正犯罪構成”,以“證明”其具有可罰性。但預備行為和未遂行為、中止行為一樣,其可罰性的前提條件是犯罪行為停滯在預備或未遂、中止階段,既遂后就談不上預備行為或未遂行為的修正犯罪構成問題了,既遂了就不存在處罰預備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的問題,這里用不著用既遂行為“吸收”預備行為、未遂行為和中止行為進行解釋。換句話說,處罰預備行為或未遂行為就是因為預備行為或未遂行為沒有既遂而又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既遂后懲罰預備行為是荒謬的,因為懲罰預備行為的前提條件就是其沒有既遂,否則預備行為不可罰。說既遂行為“吸收”預備行為,是可笑的,好像預備行為仍然可罰,只不過被既遂行為“吸收”了、“消化”了。準確地說“既遂”是一種狀態,既遂不是預備,既遂也不是未遂,既遂狀態不包含預備狀態,也不包含未遂狀態。你可以說由預備狀態發展到既遂狀態,但不能說既遂吸收了預備。正如你不能說晚年“吸收”了少年。因此,所謂既遂行為吸收預備行為或未遂行為,純屬濫用修辭手法。有學者舉例說張三前幾天盜竊未遂,今天盜竊既遂了,今天的盜竊罪既遂吸收前幾天的盜竊未遂,換句話說,前幾天的盜竊未遂忽略不計了。在一個具體的犯罪過程中,不存在既遂吸收未遂問題,既然既遂了,肯定不存在未遂行為需要處罰的問題,因此既遂吸收未遂是偽命題。對于今天的盜竊既遂吸收前幾天的盜竊未遂,看起來符合既遂吸收未遂的理論,實際上這是連續犯的問題,如果前幾天盜竊既遂了,今天盜竊既遂了,不是今天的盜竊既遂吸收了前幾天的盜竊既遂,而是作為連續犯,排除適用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前幾天盜竊未遂也是連續犯的一種犯罪階段,作為連續犯處理即可,沒有必要創立“既遂吸收未遂”的似是而非的規則。所謂的“實行吸收預備”也是這類似是而非的吸收規則。在同一個具體犯罪過程中,如果進入實行階段了,顯然不處罰預備階段的行為。之所以處罰預備階段行為,就是因為其沒有進入實行階段。
【案例】被告人在6月至10月期間,在東京和樺太五次試著毒死同一被害人。對此事案,大審院的判例認定為一個殺人既遂罪。即最后的殺人既遂行為吸收了之前的四個殺人未遂行為,僅以一個殺人罪(既遂)論處即可。第一次行動未遂,第二次既遂了,是否存在既遂吸收未遂的規則?如果第一次盜竊行動既遂,第二次盜竊行動也既遂了,是否存在既遂吸收既遂的規則?其實,這些問題都是連續犯里需要討論的問題,即連續犯作為同種數罪不數罪并罰,按照一罪定罪處罰,這是我國刑法的規則。因此,用不著構造出“既遂吸收既遂”的規則,也用不著構成出“既遂吸收未遂”的規則。同理,不需要構造“既遂吸收預備”的規則。
5.2.6 “吸收犯之數個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作用大小顯有差別, 因而形成高度行為對低度行為的吸收,使低度行為包括地評價在高度行為之中,僅以高度行為一罪論處。而所謂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是指從犯罪性質、 犯罪情節、 社會危害性程度和法定刑等各方面綜合權衡,刑事責任大的吸收刑事責任小的。 因此,這里的高度行為或者低度行為是個綜合指標。” (吳振興: 《罪數形態論》)
黃京平教授認為,只有數個犯罪行為所符合的犯罪構成之間具有特定的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從而導致其中一個犯罪不具有獨立性而被另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犯罪行為吸收的時候,才存在吸收關系。一個犯罪行為不具有獨立性,而另一個犯罪行為具有獨立性,前者以不同的表現形式依附于后者而存在。
總共14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上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