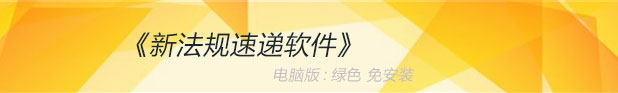[ 溫躍 ]——(2025-11-4) / 已閱8625次
12. 實質競合與數罪并罰規則
【案例】張三盜竊后發現屋里還有一個年輕女子在睡覺,就強奸了該女子。張三的盜竊行為觸犯了盜竊罪,強奸行為觸犯了強奸罪,數個罪過,數個行為,觸犯數個罪名,以盜竊罪和強奸罪宣告并適用數罪并罰規則量刑。
【案例】甲以傷害的故意將乙打傷,然后又產生殺人的犯意,于是將乙殺死。其客觀上只造成了乙死亡這一個現實危害結果,但由于前后有傷害殺人兩個主觀意思以及兩個身體動作,所以是多個行為觸犯數個罪名,屬于實質數罪,且適用數罪并罰規則。
【案例】行為人甲由于與乙結仇,將乙家一貴重古董花瓶從高空拋落,在乙路過時將其砸死。行為人丙由于與乙結仇,將乙家一貴重古董花瓶摔碎,同時從高空扔下大塊石頭將乙砸死。前者是想象競合犯,后者是實質競合,適用數罪并罰規則。
12.1李斯特認為:“實質競合是指數個獨立的應受處罰行為的實際上的競合。如果此等數行為屬于同種,則稱之為同種實質競合,如果不同種,則稱之為異種實質競合。在同一行為人實施數個犯罪行為情況下,每個犯罪均應科處相應刑罰,因此,犯罪行為之數量應當與刑罰之數量相等的合乎邏輯的思想,根據現行立法中的主流觀點,必將導致有期自由刑的執行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嚴厲。減輕刑罰嚴厲程度的法律規定要求從法律上確定減輕處罰的先決條件,并導致人們建立競合的概念。”(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P398)
12.2 所謂實質竟合是指行為人用多個行為觸犯了多個刑法規范。實質性的同種數罪的競合如一個人多次實施搶劫,這部分內容我們放在了連續犯或同種數罪部分討論了。下面著重討論異種數罪的實質競合:數行為觸犯數罪名,并適用數罪并罰規則。
12.3實質競合的先決條件首先是存在數個行為(行為復數),其次存在同時受審判的可能性。并非每一個行為復數都將必然地適用關于實質競合的數罪并罰的量刑規定。這可能是,因為存在將行為復數視為法條單數,也可能存在缺乏在同一訴訟程序中一起受審判的可能性的情況。在德國法中,駕駛中實施的數起交通違法行為原則上是行為復數。過失危害交通安全和非法逃離交通肇事現場構成行為復數,酒后駕駛(導致發生交通事故)和逃離交通肇事現場同樣構成行為復數。相對于持有麻醉品而言,繼續轉讓麻醉品是一個獨立的犯罪,因而構成行為復數。
12.4 涉及最高之個人法益的,如果具體的行為是針對不同的法益享有人,排除連續行為,作為行為復數處理;殺死不同之人;對不同的兒童為性虐待;強奸不同的婦女;猥褻不同之人。在最高之個人法益情況下,每一個具體行為,無論是行為不法和結果不法,還是行為的罪責內容,在判決中均必須分別作出確認和評價。我認為德國法在涉及最高個人法益的故意犯罪上,排除了連續犯的適用,作為行為復數,按照實質數罪,采用數罪并罰規則。在上述情形下,我國刑法是排除數罪并罰規則適用的。
12.5 我國刑法數罪并罰規則的修法建議
12.5.1我國刑法第六十九條:“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我認為數罪并罰限制在25年之下是錯誤的。比如一個被告人觸犯幾項重罪都在10年以上的量刑,總和刑期在35年以上,按照減刑和假釋的規定,最低期限是當其服刑一半即12.5年就能夠因減刑出獄或假釋。判處無期徒刑的,最低期限是服刑13年就能夠減刑出獄或假釋出獄。判處死緩的,2年期滿以后,不論減為無期徒刑或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實際上是在13年或12.5年之上加2年,即死緩最低服刑期限是15年。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不論你觸犯多少重罪,不論殺人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只要不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判死緩最短坐牢期限是15年,判低于死緩的自由刑,最短坐牢期限更少。對于一個二、三十歲的犯罪分子來說,15年之后正當年,完全可以盡享人生,如再犯又是一條好漢!當然,一般犯罪分子實際坐牢時間稍微長一點,取決于他在監獄中的表現和立功表現,不可能踩點減刑等。據說我國一個省內所有監獄里犯人中包括在獄中犯新罪加刑的在內實際服刑超過20年的才21人,超過25年的4人,最長服刑期限是29年。整個刑罰體系在自由刑上如此草率,就特殊預防來看,對很多重罪犯罪人阻卻其再犯的功效很低;就一般預防來看,實際坐牢十幾年能嚇唬誰?如今,各國人的壽命已經延長了很多年,對于很多犯罪人來說,坐牢十幾年完全在其生命可承受之重范圍內,因此各種犯罪此起彼伏,前赴后繼。歐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有期徒刑不是無聊的設計,而是在減刑和假設制度下有意義的。以輕刑化為方向的刑罰改革實際上在虛偽的人道借口下抹殺了刑罰的威懾力,西方國家高犯罪率與輕刑化方向是分不開的。人道的刑罰和社會安全的維護是兩極張力,很難價值取舍,其現實的平衡程度是個社會共識問題,即社會大多數成員要求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更安全還是更自由更人道?我不認為大多數成員的要求就是正確的,但大多數成員的意思在民主社會里決定了社會共識和社會制度及其結構的形式。
12.5.2我國刑法第69條第3款:“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其中附加刑種類相同的,合并執行,種類不同的,分別執行。”即數罪并罰時,死刑、自由刑與作為附加刑的或作為獨立刑的沒收財產、罰金刑并科。如果數罪中有一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并罰時應只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數個剝奪政治權利的,在數個剝奪政治權利年限中最高年限之上,10年以下,由法官裁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條規定“依法對犯罪分子所犯數罪分別判處罰金的應當實行并罰,將所判的罰金數額相加,執行總和數額。即數個罰金刑的,采取累加并科。德日刑法的罰金與無期徒刑不并科的規定,我國不該采納,因為我國的無期徒刑并不是終身監禁,只是一種變相的有期徒刑。如果死刑能夠與罰金刑并科,那么無期徒刑與罰金刑并科就更加無障礙了。我認為罰金是對犯罪人合法財產的剝奪,如果犯罪人有財產,即使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包括不得減刑的終身監禁),剝奪其合法財產,收繳其罰金都是能夠執行的。誤以為罰金是在犯罪人出獄后才執行時,才會主張罰金與無期徒刑不并罰。沒收財產與罰金不能分別執行,只應該執行沒收財產。
12.5.3 一個犯罪行為在未執行完畢之前,或在時效屆滿或被赦免前,原判以前的異種犯罪被發現,前后罪先并罰然后減去已經執行的刑期;一個犯罪行為在未執行完畢之前,或在時效屆滿或被赦免前,原判以前的同種犯罪被發現,同種的前后罪從重或加重處罰,然后與異種犯罪數罪并罰再減去已經執行的刑期;在判決確定后,刑罰未執行完畢之前又犯新罪(不論同種異種),與未執行的刑期并科相加,以總和刑期作為執行刑期。先減后并使得執行完畢之前犯罪實際服刑低于執行完畢之后犯罪,這是不合理的,因為刑罰執行完畢前再次犯罪,表明犯罪人在服刑期間仍不思懺悔,不遵法紀,具有深重的人身危險性和反社會性,應對其再次犯罪予以嚴懲,不應使其享受數罪并罰制度所帶來的利益,而且在被監管之下的犯罪受到的處罰應該重于釋放后的犯罪。因此,我認為不把判決生效后未執行完畢之前又犯新罪納入數罪并罰是合理的,實際上我主張取消先減后并,一舉解決了張明楷教授提出的因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第69條第1款所增設的“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的規定,形成的采用“先減后并”方法時,總和刑反而可能達不到35年以上,因而最多只能合并執行20年倘若先前執行的刑罰沒有超過5年,就會輕于“先并后減”問題(張明楷《數罪并罰的新問題》)。《英國刑法匯編》第33條:已受監禁之處罰,再犯重罪者,法院得再判監禁,候原刑期屆滿后執行之)。日本刑法典第45條合并罪規定“未經確定裁判的兩個以上之罪,構成合并罪。”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典第50條數罪并罰之要件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合并處罰之。”由此可見,在我國臺灣地區行為人在裁判確定后另犯有其他罪的,是不在數罪并罰規定之列的。
刑罰執行完畢之后又犯新罪,單獨定罪量刑,不存在數罪并罰問題。
12.5.4由于我國的有期自由刑包括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三種。對于一行為人犯有數罪被判處數種類型的有期自由刑的情形,《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69條中增加了一款作為第2款:“數罪中有判處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執行有期徒刑。數罪中有判處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執行完畢后,管制仍須執行。”這種有期徒刑“吸收”拘役,不“吸收”管制的做法,引發了學術界的爭議。張明楷教授認為:A犯甲罪與乙罪,分別定罪量刑時,原本應分別判處甲罪有期徒刑6個月、乙罪拘役5個月, 在乙罪只能判處拘役時,就不能因為拘役要被吸收,便對甲罪從重處罰。同樣,當乙罪只能判處拘役時,也不能因為拘役會被有期徒刑吸收,而將原本應當判處拘役的乙罪判處管制。張明楷教授以“一罪一刑”的罪刑關系原理決定了乙罪的刑罰不能影響甲罪的刑罰,從而禁止法官做出上述判決。張明楷教授為何不從法官的道德角度禁止法官做出對被告人不利的判決呢?因為法官缺乏對被告人家屬的同情心,只想著重判被告人,顯然缺乏道德感。其實,這里出現的問題是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有期徒刑“吸收”拘役引起的。類似的問題也會出現在無期徒刑吸收有期徒刑上。比如,A犯甲罪、乙罪和丙罪,分別定罪量刑時,原本應分別判處甲罪無期徒刑、乙罪有期徒刑15年,丙罪有期徒刑15年。根據無期徒刑“吸收”有期徒刑的規定,數罪并罰執行無期徒刑,乙罪和丙罪的有期徒刑15年被“吸收”了。如果法官覺得這樣放縱了被告人,為了重判被告人,把甲罪無期徒刑改為15年有期徒刑,甲罪、乙罪和丙罪數罪并罰,總和刑期達到45年,法官在15年之上,25年之下量刑。A犯的實際服刑年限可能高于只判甲罪的無期徒刑。由此可見,采取同刑種的“吸收原則”都會出現這種情形,很難指控法官把甲罪的無期徒刑改為15年有期徒刑是違反“一罪一刑”的罪刑原則,更難指控法官判甲罪15年有期徒刑是受乙罪和丙罪15年有期徒刑的影響,為了規避有期徒刑被無期徒刑“吸收”而做出的改動。由于張明楷把刑法修正案當成“圣經”來看待的,不敢動圣經,只好挖空心思找到“一罪一刑”的罪刑關系原理來禁止法官加重刑罰的操作。在我看來,刑法修正案九規定有期徒刑吸收拘役不合理;兩者并科,先執行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后再執行拘役也不合理。我建議在數罪中含有期徒刑與拘役并罰時,把拘役刑期視為短期有期徒刑刑期,幾個有期徒刑刑期一起相加,在總和刑期之下,數罪中最高刑之上,由法官自由裁量宣告刑。即用有期徒刑的限制加重原則,替代有期徒刑對拘役的“吸收原則”。這樣的數罪并罰規則相對合理,又不會勾引法官出于避免乙罪的拘役被甲罪的有期徒刑吸收考慮而把甲罪的有期徒刑改為拘役。至于無期徒刑“吸收”有期徒刑問題導致的不公,我認為用建立刑種升級制度來解決。比如,兩個或三個以上死緩升格為死刑立即執行;兩個或三個以上無期徒刑升格為不得減刑假釋的無期徒刑;兩個或三個以上13年以上有期徒刑升格為無期徒刑。建立幾個拘役升格有期徒刑的具體制度,幾個管制升格拘役的具體制度。
13. 本文總結:
13.1如果說共同犯罪理論是數個行為主體共動觸犯一個罪名時,如何分配罪名和罪責的理論,那么罪數(競合)論就是一個行為主體觸犯了數個罪名時如何分配罪名和罪責的理論。
13.2其實,罪數論區分一罪與數罪,并不是理論上關心犯罪人究竟構成一罪還是數罪,而是對于一個犯罪主體觸犯多個罪名時,原則上是數罪并罰的,但對于雖觸犯數個罪名但實質上是一罪,或根據一些規則按一罪處罰,或按照立法規定按照一罪處罰,這是罪數論要討論的問題,即罪數論是數罪并罰的例外理論。競合論實際上從另一角度(競合角度)討論數罪并罰的例外規則。
13.3張明楷教授認為“一罪與數罪的區分標準只能根據犯罪的本質予以確定,而不是以最終是否并罰來確定。”山口厚教授認為 “這樣,即便是那些只觸犯一罪名而完全無應否并罰疑問的情形,如“單純一罪”,也必須在罪數論中討論。”我認為張明楷教授和山口厚教授在罪數論的功能上存在認識誤差。罪數論研究一罪和數罪完全是為了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只有從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的功能角度,才能合理解釋罪數論的架構和內容,而不至于陷入繁瑣無用的理論構造之中。
13.4在討論罪數問題時,分為兩種情形討論:
一、一行為下的數罪并罰規則的排除適用問題:
(一)在一行為下行為人觸犯一罪名的構成要件;
(1)一行為觸犯一罪名的普通犯,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比如,一槍打死一人。沒有爭議,在罪數競合論中沒有討論必要。徐行犯是多次行為作為整體看待符合構成要件行為,也屬于一行為觸犯一罪名,排除適用數罪并罰規則。
(2)一行為延續不中斷觸犯同一罪名的繼續犯,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比如,非法拘禁。繼續犯作為一罪不適用數罪并罰是沒有爭議,但一旦否定某罪是繼續犯,就面臨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問題。因此罪數競合論中有討論必要。
(3)一行為表面觸犯數罪名實質觸犯一罪名的法條競合犯,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比如,保險詐騙罪與詐騙罪。法條競合只適用特殊法的罪名,不適用一般法的罪名,仍然成立一罪,不適用數罪并罰規則。法條競合犯存在一系列誤解,因此在罪數競合論中法條競合犯有討論的必要。
(二)在一行為下行為人觸犯數罪名的構成要件。
(1)異種罪的想象競合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而擇一重罪從重或加重處斷,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比如,盜竊罪與破壞電力設備罪。
(2)同種罪的想象競合犯:一行為觸犯同種數罪名而按一罪從重或加重處斷,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比如,扔一顆手榴彈炸死五人。
想象競合犯存在一系列誤解,因此在罪數競合論中想象競合犯有討論的必要。
二、數行為下的數罪并罰規則的排除適用問題:
(一)數行為觸犯數罪名且不適用數罪并罰規則。
(1)數行為觸犯數罪名的牽連犯,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我主張廢除牽連犯概念,把立法和司法解釋中作為一罪處罰的目的與手段行為或結果行為納入共罰行為框架處理。
(2)數行為觸犯數罪名的吸收犯,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我主張廢除吸收犯概念,把立法和司法解釋中作為一罪處罰的“吸收行為”納入共罰行為框架處理。
(3)數行為觸犯數罪名但立法直接規定為一罪從而排除數罪并罰規則的適用:結合犯、包容犯、結果加重犯、轉化犯等。我主張罪數競合論中保留這部分內容,作為法定一罪的組成部分,排除適用數罪并罰規則。對于結果加重犯來說,加重法條與基礎法條之間是想象競合關系,當不滿足加重法條時,可以適用基礎法條處罰。故意傷害致死是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故意傷害致死仍然屬于故意傷害罪。量刑規則與基礎法條之間是同一罪名,因此可以看成是法條外延上的種屬關系,當不符合量刑規則加重處罰時,可以適用基礎法條定罪處罰。這里不是法條競合關系。
(4)數行為觸犯數罪名,在社會共識和司法傳統中作為一罪處斷而忽略其他罪行的共罰行為。我認為共罰行為包括伴隨犯、事后不可罰行為、立法或司法解釋規定按一罪處斷的牽連犯和吸收犯等。
(二)數行為觸犯一罪名且不適用數罪并罰規則。
(1)數行為多次觸犯同一罪名的連續犯,我反對模擬為一罪處理,主張以同種數罪按照一罪從重或加重處罰。
(2)慣犯、常習犯、職業犯、營業犯等都是數行為觸犯同一罪名,都是同種數罪的細分類別,差異在犯罪的目的等(從罪數論來看,這種區分沒有必要),這類排除數罪并罰是我國司法共識,只是按照一罪從重處罰而已。集合犯是常習犯、職業犯、營業犯的上位概念,也該一并取消。
總共14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上一頁 下一頁